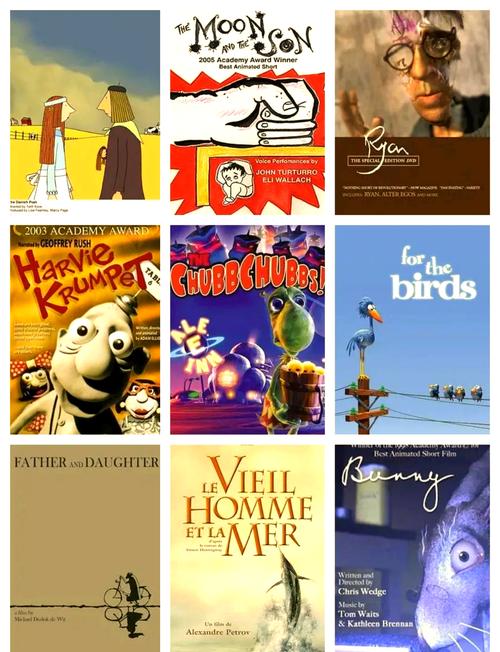云层像被揉皱的白报纸,两架战斗机在上面撕开长长的口子。红桃A的徽章在机翼上闪,黑桃K的尾翼冒着黑烟,子弹像愤怒的蝗虫,密密麻麻扑向对方驾驶舱。
“狗娘养的黑桃!”红桃飞行员咬碎嘴里的雪茄,操纵杆猛地一拉,飞机擦着对方的机翼翻了个跟头。他看见黑桃飞行员的脸贴在玻璃上,眼神像要吃人——他们在军校时是同桌,现在却要把对方轰成碎片。
爆炸声震碎了耳膜。红桃的油箱被击中,飞机像断线的风筝坠向海面,他在昏迷前最后看到的,是黑桃的飞机也冒着火跟了下来。
醒来时,沙子正往嘴里钻。红桃摸了摸断了的胳膊,看见不远处的椰子树下,黑桃正用刺刀撬椰子,动作笨拙得像头熊。“还没死?”他吼了一声,摸向腰间的枪,却发现只剩个空枪套。
黑桃转过头,脸上有道血痕,嘴角却勾着笑:“死不了,你呢?”他扔过来半个椰子,“这里没红桃也没黑桃,只有两个快渴死的蠢货。”
头三天,他们用石头画了条楚河汉界。红桃睡东边,黑桃睡西边,捡贝壳都要分清楚是谁先看见的。直到暴雨冲垮了“国界”,黑桃发了高烧,红桃犹豫了半天,还是把他拖进自己用芭蕉叶搭的棚子。
“我爹是被你们红桃的炸弹炸死的。”黑桃烧得迷迷糊糊,抓着红桃的手腕说。红桃没说话,只是往他额头上敷了块凉海草——他的弟弟,死在黑桃军队的枪下。
转机是只受伤的海鸟。它翅膀流着血,扑腾到两人中间。黑桃刚要伸手,红桃按住他:“别动,我来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拔掉鸟翅膀上的弹片,凤娃的治愈之火?不,这里只有他笨拙的手指和黑桃递过来的草药。海鸟飞走那天,他们第一次坐在同一块礁石上,看夕阳把海水染成金红色。
四个月后,搜救船来了。红桃和黑桃站在岸边,看着船上飘扬的红桃旗帜,又看了看对方。黑桃突然笑了,掏出藏在怀里的半张扑克牌——是红桃A和黑桃K粘在一起的样子。红桃也笑了,从口袋里摸出另一半,拼在一起,正好是个完整的方块。
船越来越近,扩音器里喊着他们的编号。红桃和黑桃对视一眼,同时转身,往荒岛深处走去。海浪拍打着礁石,像在鼓掌,又像在叹息。
后来,没人知道那两个飞行员去了哪里。只听说在那座荒岛上,有人见过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,一个在烤鱼,一个在修木筏,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连在一起的两个字母——不是A,也不是K,是个大大的“人”字。




![紫川 全42集 [动画]](https://l6.fi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2025081610341667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