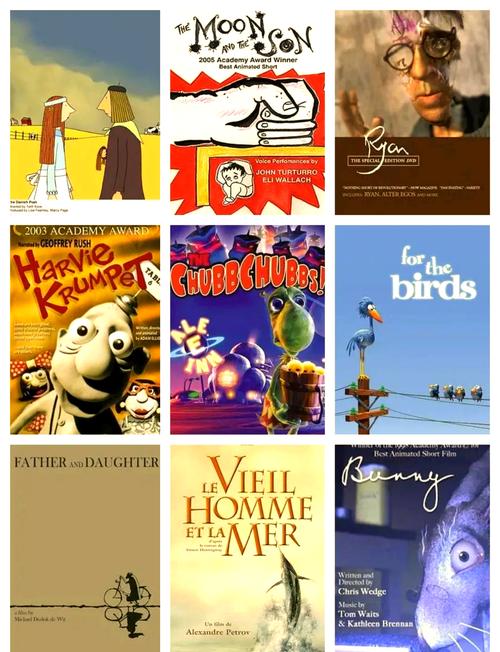青山宗的云总是淡的,像神末峰弟子洗得发白的道袍。井九站在崖边,指尖捻着片刚落的松针,看着远处各峰弟子御剑掠过,剑穗上的玉坠在阳光下晃成碎金——他们是来参加“问道大会”的,而他这个神末峰唯一的弟子,连佩剑都还没选好。
“听说了吗?景阳真人飞升时被白仙人暗算,神魂俱灭呢。”低低的议论声顺着风飘过来,井九捏松针的手指紧了紧。他记得那道贯穿胸膛的白光,记得神剑“万物一”刺入自己神魂时的灼痛,更记得白仙人面具上那道月牙形的疤。
赵腊月是第一个闯上神末峰的。小姑娘背着比人还高的剑匣,额角带着伤,眼睛却亮得像星:“我要拜你为师!”井九没理她,转身往洞府走,却听见身后“哐当”一声——她竟把剑匣往地上一砸,直接盘腿坐下,“你不收我,我就饿死在这儿。”
三日后,井九扔给她一把木剑。赵腊月练剑时总爱喊,剑气劈得崖边碎石乱飞,井九就在旁边煮茶,看她把“青山九式”练得虎虎生风,偶尔淡淡说句:“手腕再沉三分。”柳十岁来的时候更安静,这孩子背着个药篓,见人就脸红,却能准确报出峰上每种草药的习性,井九让他打理药圃,他便把那里侍弄得比谁的剑穗都整齐。
问道大会上的麻烦来得猝不及防。上德峰的弟子指着井九的鼻子骂“野种”,说神末峰早该除名。赵腊月当场拔剑,木剑撞上对方的精铁长剑,“咔嚓”断成两截。井九这时才站起身,随手捡起块石子,屈指一弹——石子穿过层层剑光,正打在对方剑柄的凹槽里,长剑“当啷”落地。“比剑,”他看着脸色铁青的上德峰长老,“还是比扔石头?”
真正的凶险藏在不老林的迷雾里。太平真人的傀儡术出神入化,那些用活人炼制的“行尸”,脸上还挂着生前的表情,指甲却比剑还利。井九第一次对上它们时,赵腊月被缠住,柳十岁吓得腿软,他却突然想起“万物一”的剑意——不是斩,是融。指尖划过虚空,无形的剑气像水流般漫过,行尸瞬间化为齑粉。“别怕,”他回头看两个浑身发抖的孩子,“它们怕光。”
后来他们去了外界,在那个用科技伪装修行的世界,井九看见飞行器拖着尾焰划过夜空,像极了当年景阳真人飞升时的轨迹。白仙人就藏在最高的那座塔上,隔着百米光幕,声音冷得像冰:“你以为重生就能改变什么?这天地,本就是个牢笼。”
井九没说话,只是拔出了“万物一”。神剑嗡鸣着,剑身映出三个身影——他自己,还有身后握紧剑的赵腊月和柳十岁。剑光起时,云雾散开,塔尖的伪装卸下,露出里面生锈的锁链。原来所谓“飞升”,不过是被更高存在锁住的开始。
当最后一条锁链断裂,井九望着真正的星空,突然觉得神末峰的云也没那么淡了。赵腊月拍他的肩膀:“师父,接下来去哪?”柳十岁捧着新采的草药,眼里闪着光。他笑了笑,这是重生后第一次笑:“先回去,把药圃的篱笆修了。”
风吹过崖边,松针落在井九的发间,像极了很多年前,景阳真人还在时的模样。有些道,从来不是往天上走,而是带着身后的人,一步步把脚下的路走成坦途。




![紫川 全42集 [动画]](https://l6.fi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2025081610341667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