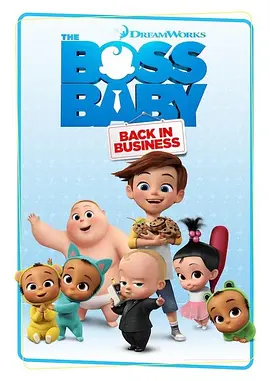无限列车的汽笛声撕开夜幕时,炭治郎正把祢豆子的木箱塞进座位底。车厢里的温度骤降,善逸抱着手臂发抖:“总觉得……有人在盯着我们看。”伊之助的野猪头套突然转向过道尽头,“哼,有股臭烘烘的血腥味。”
炼狱杏寿郎的披风像团燃烧的火焰,他端着便当盒大步走来,饭盒里的鲑鱼饭冒着热气:“少年们,饿了吧?先吃点东西!”他的笑声比列车的轰鸣还响,可当他看向窗外掠过的树影,瞳孔突然收缩——那些树的形状,像极了扭曲的人体。
午夜的钟声敲到第三下,乘客们的呼吸变得均匀得诡异。炭治郎刚想叫醒邻座的老人,眼皮就重得像灌了铅。梦里的雪是暖的,妈妈正把烤红薯塞进他手里,弟弟妹妹围着灶台转圈,祢豆子的笑声脆得像风铃。“别走了,炭治郎。”妈妈的手抚过他的头发,“留在这里,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他的指尖刚触到红薯皮,突然闻到一丝血腥——那是爸爸临终时,咳在他衣袖上的味道。
“不对!”炭治郎猛地睁开眼,日轮刀劈开座椅,露出底下蠕动的肉色丝线。善逸还在梦里哭喊:“我不想再被人说没用!”伊之助的斧头在幻境里劈砍空气,嘴里吼着“再来啊”。而炼狱已经站在过道中央,炎之呼吸的火光把车顶照得通红:“魇梦!你的鬼术对我没用!”
丝线突然暴起,刺穿乘客的身体,把他们变成直挺挺的傀儡。炼狱的刀横扫,火焰斩断丝线的同时,也烧焦了自己的手臂。“保护好他们!”他对着炭治郎大吼,披风被傀儡的利爪撕开,却半步没退。炭治郎咬着牙唤醒善逸,伊之助的头套被自己的斧头劈开,清醒的瞬间就扑向最近的傀儡。
当魇梦的本体从列车连接处爬出来,炭治郎才发现这只鬼没有脚,身体像条黏腻的蛆虫。“你们逃不掉的。”魇梦的声音从无数张嘴里同时发出,“这列车就是你们的坟墓。”可他没看到,炼狱的刀已经蓄满了火,那火焰里映着无数乘客的脸——有抱着婴儿的母亲,有背书包的少年,有拄拐杖的老人。
“炎之呼吸·玖之型·炼狱!”
火光冲天时,炭治郎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。不是魇梦的,是炼狱的。鬼的血溅在他脸上,烫得像岩浆。当魇梦的头颅落地,列车的警报声突然变得凄厉——猗窝座的身影出现在烟雾里,拳头上还沾着炼狱的血。
“你很强,”猗窝座的眼睛亮得像野兽,“成为鬼吧,我们能永远战斗。”
炼狱的刀插在地上,支撑着他半跪的身体。血从嘴角涌出来,他却笑了:“我拒绝。”阳光刺破云层的瞬间,他的目光扫过炭治郎、善逸、伊之助,最后落在木箱上:“少年们,要让更多人幸福啊。”
列车到站时,炭治郎把炼狱的羽织叠得整整齐齐。善逸在哭,伊之助的拳头捏得发白,祢豆子从木箱缝隙里伸出手,指尖沾着一滴眼泪。炭治郎摸着羽织上的火焰纹章,突然明白:所谓传承,不是记住死亡,是带着逝者的信念,继续往前跑。
酷漫简日的特效字幕在屏幕上炸开最后一朵火花,像极了炼狱留在世间的最后一点光。





![紫川 全42集 [动画]](https://l6.fi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2025081610341667.png)




![86-不存在的战区 [日漫]](https://l6.fi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2025081517590270.web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