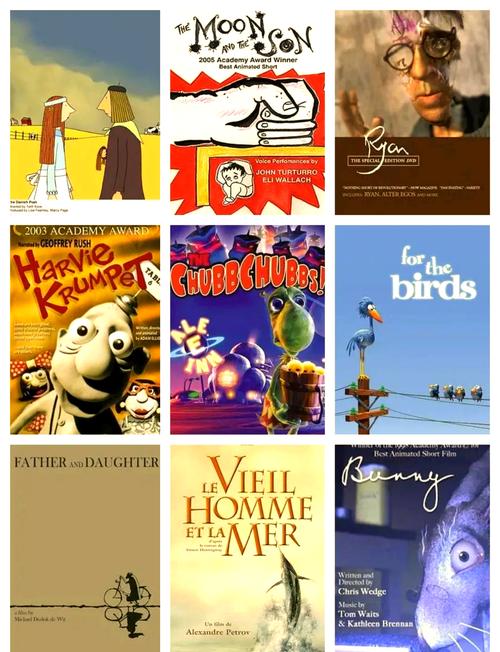漠北的风裹着沙砾打在李星云脸上时,他正蹲在阴山的断碑后,看着远处述里朵的营帐飘起玄黑色旗帜。不良帅的斗笠压得很低,遮住半张脸,只有嘴角那道新添的伤疤在月光下泛着白——那是被多阔霍的骨刃划开的,此刻还在隐隐作痛,像在提醒他坠崖时的绝望。
“四月会要开始了。”侯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他指尖转着骨笛,衣摆上沾着没擦净的血,“述里朵要集齐八枚魃阾石,听说那东西能让死人睁眼,提着刀接着砍。”李星云没回头,只是摸出腰间的酒葫芦,灌了口烈酒,酒液顺着伤疤渗进去,疼得他龇牙咧嘴,却笑了出来:“不死战兵?她当这是过家家?”
话音刚落,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。姬如雪的身影从风沙里钻出来,玄甲上结着薄冰,她翻身下马时,披风扫过李星云的斗笠:“奥姑在萨满庙杀了三个部落首领,尸体都被拖去喂狼了。”李星云捏紧酒葫芦,葫芦上的裂痕又多了几道——那是他坠崖时攥碎的,“她不是述里朵的人?”
“谁知道呢。”姬如雪解下腰间的短刀,刀鞘上还沾着萨满庙的朱砂,“降臣托人带了话,说要跟你赌一局。她给你两枚魃阾石,你帮她把多阔霍的残臂找回来。”李星云猛地抬头,斗笠滑落,露出眼底翻涌的黑气——那是九幽玄天神功在作祟,“她倒会算计。”
夜里潜入述里朵营帐时,李星云差点撞上奥姑的银甲。那女人背对着他,正用骨针在羊皮卷上绣阵图,针尖刺破的地方渗出暗红的血,在灯下像极了活物。“不良帅的脚步声,比草原上的孤狼还轻。”奥姑突然开口,骨针没停,“可你眼底的魔气,藏不住。”李星云握紧身后的龙泉剑,却见她转过脸,额间的图腾在火光里明明灭灭:“你以为述里朵真信那玄冥大阵?她要的,是让中原人看一场‘不死’的笑话。”
帐外突然响起厮杀声。侯卿的骨笛混着萤勾的尖啸刺破夜空,李星云趁机掀翻案几,羊皮卷上的阵图在混乱中被火星点燃,烧出一串诡异的符文。述里朵的笑声从帐外传来,带着金铃般的脆响:“李星云,你的不良人,怕是要变成真的‘死人’了。”
李星云冲出营帐时,正撞见旱魃举着巨锤砸向多阔霍的铁骑。那汉子赤裸的胳膊上爬满尸斑,却笑得比谁都凶:“小娃娃,再不动手,姬丫头可要被奥姑的银枪挑了!”李星云仰头饮尽最后一口酒,将葫芦狠狠砸在地上,龙泉剑出鞘的瞬间,黑气从周身暴涨——他知道,这场赌局,早就没有退路。
风沙里,姬如雪的玄甲反射着刀光,张子凡的纸伞在乱军中忽开忽合,侯卿的骨笛吹出催命的调子。李星云踩着尸体往前冲,剑刃切开漠北武士喉咙时,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,袁天罡在城楼上对他说的话:“这天下,从来不是靠心软能守住的。”
当第一枚魃阾石在他掌心发烫时,李星云看着远处述里朵那张笑靥如花的脸,突然明白了——所谓的不死战兵,从来不是用石头造的,是用江湖人的血,朝廷的骨,还有每个想活下去的人,心头那点不肯熄灭的火。





![紫川 全42集 [动画]](https://l6.fi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2025081610341667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