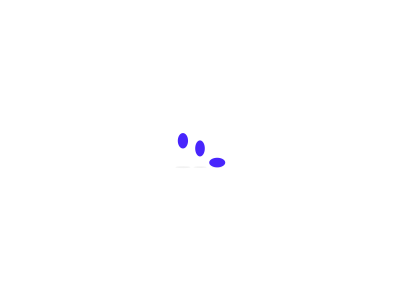灶门家的炭窑在雪夜里冒烟时,炭治郎正背着最后一筐炭往山下走。妹妹祢豆子塞给他的红薯还揣在怀里,暖得像团小太阳——他总说卖完炭就买糖给她吃,却没算到回家时,门槛上的血已经冻成了冰。
鳞泷师父的面具压得他鼻梁生疼。水之呼吸的基础动作重复了三千遍,当他终于能在瀑布里站稳,师父扔给他一把断刀:“鬼杀队的最终选拔,是让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挥刀。”紫藤花盛开的山路上,他第一次看见吃人的鬼,祢豆子从木箱里扑出来的瞬间,他突然懂了:刀是用来保护,不是用来复仇的。
善逸的雷之呼吸炸响在那田蜘蛛山时,他还在哭。“别碰伊之助!”少年闭着眼挥刀,电光劈开累的蜘蛛丝,像劈开自己多年的懦弱。后来他总说那是睡梦中的力量,可炭治郎看见他攥刀的手心,磨出的茧比谁都厚。
无限列车的蒸汽裹着血腥味,炼狱杏寿郎的炎之呼吸烧红了夜空。“少年们,”他的刀断成两截,血溅在炭治郎脸上,“要心怀大义啊。”列车到站时,炭治郎把炎柱的羽织叠得整整齐齐,那上面的火焰纹章,在月光下像团不肯熄灭的火。
游郭的红灯笼晃得人眼晕。宇髓天元的发带缠在炭治郎手腕上,音之呼吸的节奏里,他看见堕姬的腰带里藏着无数女子的哭嚎。“华丽地赢啊!”音柱断了一臂,笑声却比三弦琴还响。当刀刺穿恶鬼的心脏,炭治郎突然闻到祢豆子发间的紫藤花香——原来她早就悄悄跟着来了,藏在房梁上,指甲掐进木头里,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锻刀村的雾气里,时透无一郎的霞之呼吸像片流动的云。“你很强,”少年的刀停在炭治郎颈边,“但还不够。”直到玉壶的血鬼术炸开,霞柱的斑纹在额角亮起,炭治郎才明白:所谓天才,不过是把别人用来哭的时间,都用来练刀了。
无限城的地砖翻转时,蝴蝶忍的毒正顺着童磨的血管蔓延。“姐姐,我做到了。”她的身体在恶鬼掌心化灰,药瓶却滚到香奈乎脚边——那里面,是给祢豆子的解药。后来香奈乎开枪射穿无惨的心脏,扣扳机的手指,还带着姐姐的温度。
黎明撕破云层的那一刻,炭治郎的日轮刀插进无惨的咽喉。鬼王的黑血溅在他脸上,疼得像火烧,可他死死盯着东方:“祢豆子在等我回家。”阳光漫过废墟时,他看见炼狱的笑,忍的笑,所有逝去的人都站在光里,像在说“欢迎回来”。
多年后,炭治郎在灶门家的院子里晒炭。祢豆子抱着孩子追蝴蝶,善逸和伊之助在炭窑边吵架,声音惊飞了檐下的燕子。他摸了摸腰间的刀——那是钢铁冢师父最后打的一把,刀鞘上刻着整整齐齐的紫藤花。
风穿过炭窑的缝隙,像谁在轻轻说:“人间真好啊。”